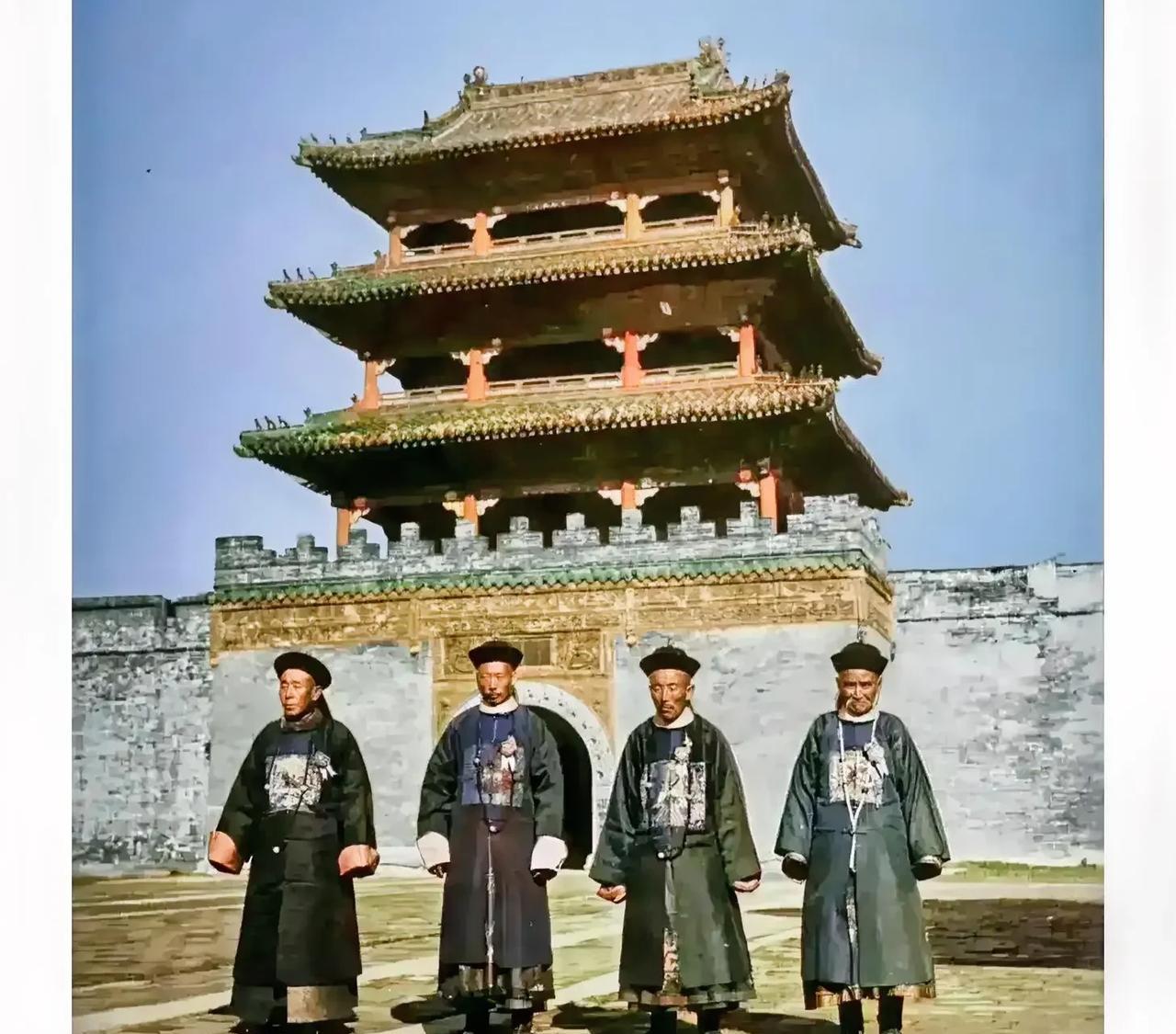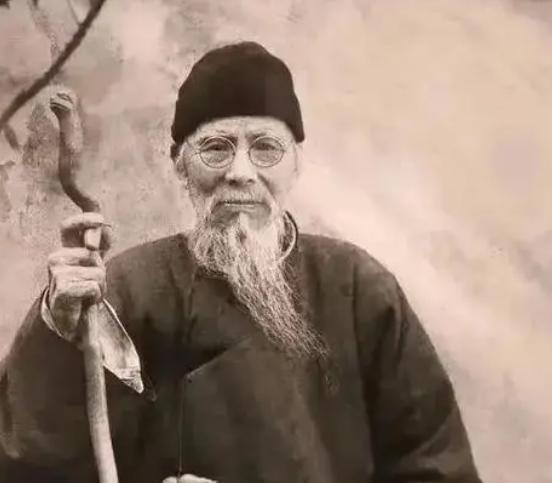新中国成立前,有那么一个职业,可谓经久不衰。无论是一片祥和的太平之世,还是饿殍满
新中国成立前,有那么一个职业,可谓经久不衰。无论是一片祥和的太平之世,还是饿殍满地的乱世,这个职业似乎都在一直延续着。这听起来好像不错,可是却是一个让人人都避而远之的职业——妓女。这个行当,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,那可是个几千年都没断过的“铁饭碗”。怪吧?天底下啥工作都可能因为改朝换代、天灾人祸给干黄了,唯独这个,生命力旺盛得跟野草似的。为啥?俩字儿:活命。太平年月,一个良家妇女,要是家里不是穷到揭不开锅,谁愿意干这个?可在那个年代,女人的地位,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她们没法像男人一样考科举、做买卖,甚至连继承家产的权利都悬。一旦家里遭了难,男人还能去当兵、卖苦力,女人呢?摆在她们面前的路,窄得可怜。被卖,或者,自己卖。到了乱世,这事儿就更残酷了。军阀混战,天灾人祸,今天这儿打仗,明天那儿发大水。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”,这话一点不假。对普通老百姓来说,活下去就是唯一的奔头。家里没粮了,怎么办?卖儿卖女。一个闺女,换几斗米,就能让一家人多喘几天气。被卖掉的女孩儿,最终的去向,十有八九就是那个不见天日的火坑。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,清末到民国时期,华北地区但凡遇到大饥荒,“鬻妻卖女”的现象就呈指数级增长。一张卖身契,就把一个女孩儿一辈子的命运给定死了。当然,也不能一概而论。这个行当里头,也分三六九等。最上等的,是那些名妓、花魁。她们大多从小被买来,琴棋书画、诗词歌对,样样都得学。她们卖的,更多是“艺”,服务的对象非富即贵,是文人墨客的红颜知己,是达官贵人的社交名片。比如晚清到民国那会儿上海滩的那些“书寓”“长三堂子”,消费高得吓人,普通人连门都摸不着。这些女性,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今天的明星,有粉丝,有话题,甚至能影响舆论。但别搞错了,她们本质上还是商品,是没有人身自由的。再风光,命运也攥在别人手里。恩客一句话,就能决定她们的荣辱生死。往下,就是咱们在影视剧里最常见的,开在闹市区的二等、三等妓院。这里的姑娘,没那么多才艺,靠的就是年轻貌美。她们每天要接待一波又一波的客人,像流水线上的零件,早就麻木了。她们的人生,就是从一个男人怀里,到另一个男人怀里,日复一日,看不到头。最底层的,叫“流莺”“野鸡”。她们连个遮风挡雨的屋檐都没有,就在街头巷尾、桥头渡口,用最卑微的方式,换取一点点能糊口的钱。她们面对的,是最大的风险和最直接的暴力,没人管,没人问。同样是“妓女”,里面的世界,比咱们想象的复杂多了。但无论哪个等级,她们的共同点都是身不由己。没人是天生愿意干这个的。每一个坠入风尘的女性背后,几乎都有一部滴着血和泪的个人史。可能有人会觉得,这都是老黄历了,跟咱们有啥关系?这个古老的职业,在新中国成立后,被以雷霆之势彻底取缔了。1949年11月21日,北京一夜之间关闭了所有妓院,解放了224名妓女。随后,上海、天津、全国各地,都开展了同样的行动。这不是简单的“扫黄”,而是一场社会改造运动。政府把这些妇女集中起来,成立“妇女生产教养院”。在里头,第一件事不是说教,而是给她们治病。旧社会的妓女,十个里有八个都带着一身的性病,梅毒、淋病,苦不堪言。新政府免费给她们治疗,用的都是当时最好的盘尼西林。第二件事,是教她们读书识字,学一门能养活自己的手艺,比如纺纱、织布、缝纫。最关键的,是第三件事:把她们当“人”看。让她们知道,自己不是商品,不是玩物,而是和所有人一样,有尊严、有权利的社会公民。很多被解救的女性,几十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,都说那是她们“重生”的开始。从“鬼”变回“人”,这是她们最常说的一句话。这场运动,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个奇迹。它告诉世界,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毒瘤,不是不能铲除,关键看政府有没有这个决心和能力。为什么今天还要聊这个?因为驱动这个古老职业背后的黑手,将女性物化、商品化的逻辑,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失。形式变了,媒介新了,但内核没变。依然是把人,特别是女性,当成满足欲望的工具和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。我们今天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妓院、没有“红灯区”的社会环境里,是无数前辈用巨大的努力换来的。这份干净,来之不易。我们回头看那段历史,不是为了猎奇,也不是为了批判谁。而是为了提醒自己:第一,要明白女性的解放和整个社会的进步是捆绑在一起的。当一个社会,能为所有女性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、就业机会和人格尊严时,那些旧时代的悲剧才不会重演。第二,要警惕任何形式的“物化”思想。无论是物化女性,还是物化男性,都是对“人”这个身份的贬低。一个人,永远不该成为另一个人的附庸或商品。